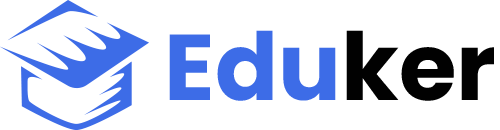古诗词里“黄鹄”到底是只什么鸟?
由于具有神性色彩的“黄鹄”意象为神鸟瑞兽,故其显现和消逝便成了福祉降临与否的征兆。“黄鹄”来则预示吉祥,离去则世道可忧,这一意义具体化为现实人世中的人际关系,其重要表现则是统治者与才士(臣子)的关系。
唐代以前的诗歌中,用“黄鹄”代才士则以楚辞《卜居》《惜誓》、魏晋阮籍《咏怀诗》、南朝江淹《古意报袁功曹诗》最为典型。“黄鹄”意象与才德之士的意义关联是由《楚辞》率先完成的。从方式上看,则主要通过比兴言志、寄托寓意以抒情的模式来构塑。《楚辞·卜居》全篇主体部分为抒情主人公心志的自我剖白,诗人提出“正言不讳以危身”与“从俗富贵以媀生”的两种人生选择,并以多种形象加以比附,前者如同“与黄鹄比翼”飞入云端翱翔,后者则似与“鸡鹜”同啄糟糠。刘良注云:“黄鹄喻逸士也,鸡鹜喻谗夫也。”借黄鹄与鸡鹜二者的云泥之别委婉纡曲表明志向。《楚辞·惜誓》中“黄鹄后时而寄处”在使用方式上与此类同,用困于“鸱鸮”的围攻中的黄鹄以自指,借助黄鹄形象进行委婉而生动的自我言说,相应的情感表达也就更加强烈而充分。黄鹄所具有的极天而飞之姿态与超拔于世之形貌能够与抒情主人公心志实现契合,从而借黄鹄之卓尔不群表现自我正直无阿、超然于世的情操和“尽忠而蔽障于谗”“谁知吾之廉贞”的苦闷。同时,才堪世用、德配人臣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与“黄鹄”形象的对应关系得到加强。
“黄鹄”意象自先秦文献既已有之,而陶婴《黄鹄歌》是目前现存文献中第一首以“黄鹄”为诗题且整首诗以黄鹄为描写主题的诗歌:
悲黄鹄之早寡兮,七年不双。宛鵛独宿兮,不与众同。
夜半悲鸣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独宿何伤?
寡妇念此兮,泣下数行。呜呼悲兮,死者不可忘。
飞鸟尚然兮,况于贞良。虽有贤雄兮,终不重行。
根据《列女传·鲁寡陶婴传》的记载,作者陶婴少寡,作此歌以明自己不再改嫁的心志。从情感特点上看,该诗歌用黄鹄悲鸣来彰显内心的孤苦,“悲黄鹄之早寡兮”“夜半悲鸣兮”“呜呼悲兮”三次用“悲”直接陈述浓郁情感,并在“呜呼悲兮”的歌咏兴叹中进行抒情主人公的情绪自我呈现。就文学手法而言,借助黄鹄以兴起全诗,且整篇诗歌以描写早寡之黄鹄的栖止游行为主要内容,用其行为特点以自比,以黄鹄之寡而不双来喻指人之寡而不续嫁的贞良。陶婴《黄鹄歌》借黄鹄以比兴的文学表达方式、哀伤的情感蕴含都具有开后世先河的典范意义;而“黄鹄”也从此成为了表现伉俪离散文学主题的典型意象。
汉代接续了陶婴《黄鹄歌》所开创的意象传统,其中《李陵录别二十首》接续离别主题,而在具体文学呈现方式上,不同于《黄鹄歌》详尽描写早寡黄鹄的“独宿”“悲鸣”等活动与“想其故雄”的心理状态呈现,《李陵录别二十首》采用大幅画面取景,而突出“徘徊”这一动作;“徘徊”即回旋飞翔之貌,用外在踟蹰不能去的动作表现内在忧伤难舍的情感。“黄鹄”意象与“徘徊”这一词汇的组合由此肇始,并在后世采用“黄鹄”意象的诗歌如“半道郁徘徊”(《黄鹄曲》)、“中道郁徘徊”(《襄阳乐》)、“将别复徘徊”(《江津寄刘之遴诗》)、“徘徊应怆然”(《中道郁徘徊》)中反复出现,而由“徘徊”之行为动作的渲染,“黄鹄”意象所蕴含的忧思和伤怀之情也得以加强。
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黄鹄歌》很可能有相当普及的流传广度。“黄鹄”意象成为忠贞之义的代表性语汇。北齐时刺史李祖牧墓志上记载李祖牧早年失去父亲,其母“黄鹄成歌,柏舟在咏”,此处“柏舟”即《诗经·柏舟》,以示“我心匪石,不可转也”,与其并列的“黄鹄”应是同义,即此墓志中的“黄鹄”意象与先秦陶婴《黄鹄歌》所表达的蕴含完全一致。这表明“黄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一种表现女性虽寡而不续嫁的象征,在广泛普及度方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堪比《诗经》,故被魏徐幹《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曹丕《临高台》,晋《黄鹄曲》,南北朝《襄阳乐》、高爽《咏画扇诗》、刘孝绰《江津寄刘之遴诗》、庾信《别周尚书弘正诗》、阮卓《赋得黄鹄一远别诗》、江总《别袁昌州诗》等数量较多的作品所直接征引。
需要指出的是,“黄鹄”意象的情感维度也在不断扩充。陶婴《黄鹄歌》中所表现的情感为夫妇之好,“黄鹄”象征忠贞不二的情操和爱侣相别的悲苦;汉、魏、晋代的创作皆承袭这一思路;至梁代刘孝绰《江津寄刘之遴诗》,始从爱情扩展至友谊,以黄鹄离别徘徊不去表达自己与刘之遴“共摛云气藻,同举霞纹杯”的深厚情谊,北周庾信《别周尚书弘正诗》、陈朝江总《别袁昌州诗二首》亦用“黄鹄”意象形容友人离别之慨,从而扩大了“黄鹄”意象在人际情感表现上的意义和范围。
在人伦关系的基础上,汉代诗歌的“黄鹄”意象在“离愁别绪”义项的系统中更有发展,由个体之间的离别难舍更扩展为人对特定地理环境的情感牵系,即乡关之思。“黄鹄”具备一飞千里,可跨越山海的超凡能力,故当诗人面对山川阻隔和遥远的地理距离所困而无法逾越,黄鹄便自然成为抒情主体歆羡和向往的对象,并进而将自我无法实现的横跨远途而抵达故土的行为举动寄托于黄鹄的形象构建之中。此种用法在唐前主要见于汉代远嫁乌孙国的和亲公主以及淮南王所作歌当中。乌孙公主为江都王建之女,汉元封中被封为公主远嫁乌孙国(《汉书·西域传》),内心寂寞孤独而倍生去国离乡之感;淮南王服食求仙,与仙人游处而不知所之,徘徊天外而生故乡之情。两诗均取黄鹄远飞之义,以黄鹄的飞翔之能对比自身局限,表现回归故土的愿景。
“黄鹄”意象经过历代文学作品的累加和强化,最终形成了该意象的特定意义内涵谱系,并通过后代诗人直接摭采并应用于诗歌的方式得以继承和稳定。唐代及以后的“黄鹄”诗歌意象无不基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歌所形成的内涵而阐发。如王维有《双黄鹄歌送别》诗,取“双黄鹄”意象“不得已,忽分飞”的凄婉之貌,促进离愁别绪“怅离忧兮独含情”的形象化表达;又如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有“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用黄鹄哀鸣比贤人君子多去朝廷以刺唐明皇,蕴藉宛转,文约义丰。
历代诗人选取“黄鹄”作为特定意志与精神的外化与载体,在构建诗歌形象世界、实现思想表达的同时,“黄鹄”意象谱系也在作品生成和层递过程中得以确立。“黄鹄”意象与诗人情感肌理结合不断趋向密切,并最终形成具有独特意义蕴含和书写形式特色的诗歌意象,随着文学流脉的传承与发展而编织形成更为丰富多元的意义系统,并在诗歌继承与创造的互动过程中愈加深化。每一首古诗中“黄鹄”振翅而摩天,实则在整个诗歌史上都引动着意义与情感的前后辉映与群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